旅途中的经历总能给人以丰厚的营养。1944年,当钱锺书被困上海写作《围城》时,他首先想到的便是1938年乘坐法国邮船回国时的情景。一开篇这样写着:“红海早过了,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,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,侵占去大部分的夜。……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(VicomtedeBragelonne)正向中国开来。”然后,便在这艘船上展开了整个《围城》的序幕,出现了船上的男男女女,精心刻画了方鸿渐与鲍小姐、苏小姐情感与关系的变化。这里的很多情形简直就是钱锺书回国时的亲历亲闻,而且,《围城》中方鸿渐的“痴气”“拙手笨脚”等种种性情为人,活活就是钱锺书本人。这便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,他们将书中的情节与作者本人的经历做对比,发现,方鸿渐留学归国后的经历基本上与钱锺书回国后的经历相合。

钱锺书曾赴牛津大学、巴黎大学留学,1938年回国后,先到上海探亲,并送前往湖南的父亲上船,紧接着赶赴昆明,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。1939年暑假,钱锺书回上海与母亲和妻儿团聚,在此期间接到父亲钱基博的来函,要他前往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。钱锺书不敢违抗父命,于是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蓝田,在湘西工作了两年,见识了很多人情世态。1941年,钱锺书再次返回上海,却正赶上珍珠港事件爆发,日本对美、英等国宣战,上海完全沦陷,钱锺书被困孤城,无法出去,由此他便经历了一段艰难岁月。
《围城》中方鸿渐也同样经历了回国、探亲、到大学任教、艰辛的旅途、困顿于上海这些经历,只不过,方鸿渐在法国邮船上是单身男,而钱钟书归国时则与夫人杨绛以及他们的孩子在一起。方鸿渐归国时还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工作,而钱钟书则已于1938年初,接到西南联大破格请他担任教授的聘书;方鸿渐虽然也有长途跋涉到地方大学任教的经历,却没有在国内一流大学担任教授的经历……那么,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该如何看待《围城》与现实生活的真真假假、互相穿插呢?
对此,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杨绛。对于《围城》中真实与虚构的交织,杨绛能像华生一样,可以将福尔摩斯探案的手法逐一分辨出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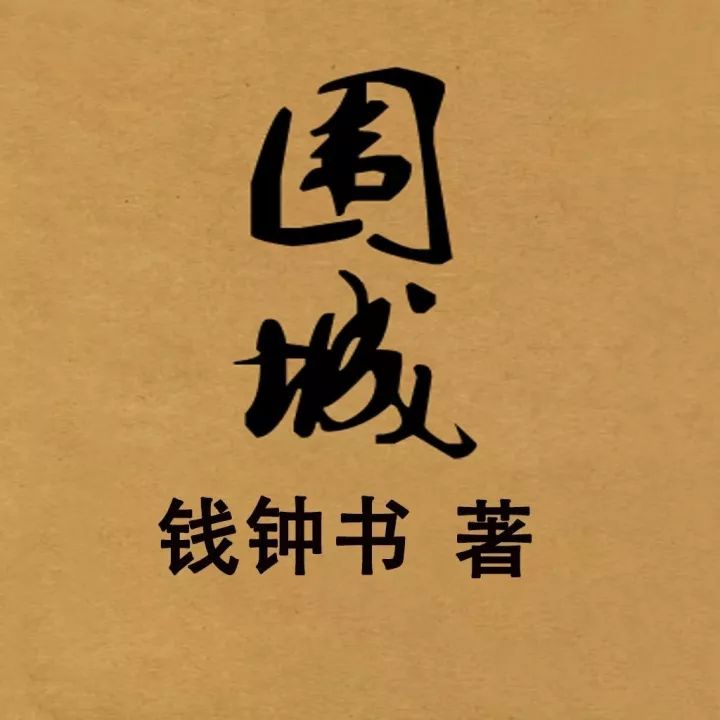
在经过很多人督促才写出的《记钱锺书与〈围城〉》中,杨绛这样说:“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(AthosⅡ)回国,甲板上的情景和《围城》里写的很像,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,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。鲍小姐却纯是虚构。……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、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。锺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,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。……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。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。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;这人可一点不美。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。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锺书央我翻译的,他嘱我不要翻得好,一般就行。”“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,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。结婚穿黑色礼服、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,不是别人,正是锺书自己。……”“《围城》的作者呢,就是个‘痴气’旺盛的锺书。我们俩日常相处,他常爱说些痴话,说些傻话,然后再加上创造,加上联想,加上夸张,我常能体味到《围城》的笔法。我觉得《围城》里的人物和情节,都凭他那股子痴气,呵成了真人实事。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,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。”
《围城》是钱锺书唯一的长篇小说,1944年动笔,1946年全部完成。这两年,钱锺书与杨绛在上海艰难度日。杨绛当家庭教师,又在小学代课,业余创作话剧。钱锺书没有工作,杨绛的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钱锺书,而钱锺书的主要时间便用在写作中。

杨绛对《围城》的诞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钱锺书称杨绛为“最才的女,最贤的妻”,事实上确实如此。她是一位才女,小的时候便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,并写出自己的好作品,到1944年的时候,她的作品已很受大众欢迎。有一次,钱锺书看了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后,回家就对杨绛说:“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。”杨绛一听,非常高兴,催促丈夫快写,然后她便将家中的所有事情都担了起来,竭尽全力支持丈夫。正如钱锺书在《围城》序言中所说:“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。两年里忧世伤生,屡想中止。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,替我挡了许多事,省出时间来,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。”
人们常说,苦难孕育着新生命。也正是在苦难中,《围城》创作完成,成为世界文坛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,不仅在中国畅销不衰,而且翻译成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日文等多种版本,在世界广泛传播。
事实上,在艰难岁月里,钱锺书还创作出一个比《围城》更重要的成果,它就是《谈艺录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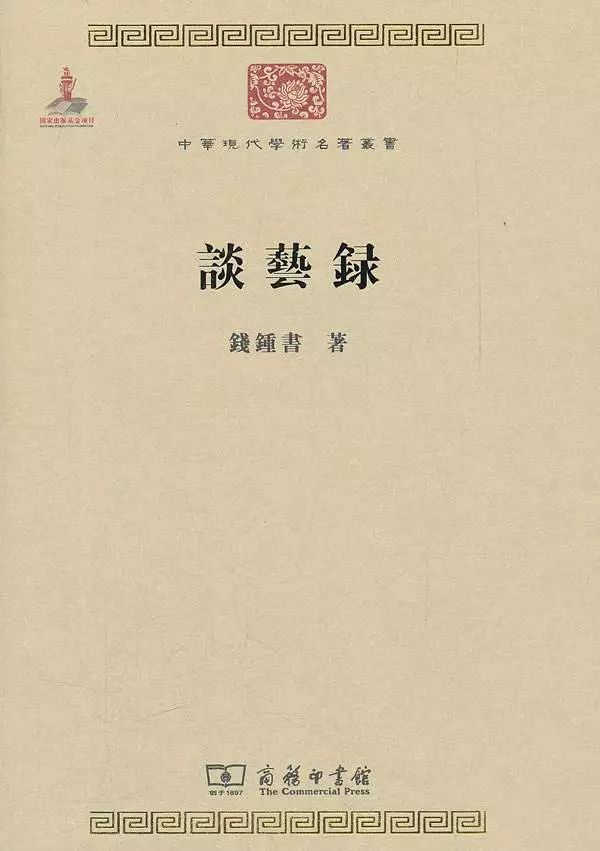
从法国乘船经过红海归国的情景,不仅出现在《围城》的开篇,同样保存在当时同船归国的冒效鲁记忆中。冒效鲁是民国大儒冒鹤亭之子,学贯中西,才华横溢,曾被前苏联汉学权威阿列谢耶夫院士称赞为“平生所见华人中不可多得的通品”。1938年,他返国途中,意外之喜就是与钱锺书相识相知。
“邂逅得钱生,芥吸真气类。”“谓一代豪杰,实罕工此事。”“凭栏钱子睨我笑,有句不吐意则那”,这些诗句都是冒效鲁写给钱锺书的,再现了他们在法国邮船上的气类相投、彼此谈诗相和的情形。也正是在彼此畅谈的过程中,钱锺书有了写作《谈艺录》的想法。1939年,钱锺书从昆明返回上海,与冒效鲁再次相见。冒效鲁极力督促钱锺书撰写书话,钱锺书颇觉技痒,于是开始了《谈艺录》的最初写作。从1939年秋到1941年夏,钱锺书在湖南蓝田师院完成了《谈艺录》的初稿,而这实际上只是全书的一半。

钱锺书被困上海后,《谈艺录》的写作变得更加重要,个人和家国都处在忧患之中,钱锺书也把《谈艺录》当成“忧患之书”,念兹在兹,不断修改,不断补订。
杨绛对《谈艺录》也非常重视。一次,两名日本宪兵奉命上门查问,钱锺书正巧不在家,而杨绛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保护好《谈艺录》。
1942年,《谈艺录》成稿,先在朋友间传播。此时,钱锺书的朋友有傅雷夫妇、楼适夷、柯灵、陈西禾等人。朋友们一边看,钱锺书一边修订。即便在创作《围城》的忙碌时期,钱锺书也没有停止对《谈艺录》的修订。经过十年的磨练,《谈艺录》才最终定稿。1948年6月,当《谈艺录》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,次年7月出版后,大受欢迎。《谈艺录》也成为钱锺书的代表作之一,是钱锺书这一时期与《围城》题材不一、但又彼此促进的一大学术工程。




